张盾,男,1956年7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历史系历史专业。1982年进入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马列部攻读硕士学位。2004年在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匡亚明特聘教授,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兼任吉林省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外审专家、中国马哲史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张盾长期从事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美学研究。出版专著《分析的限度:分析哲学的批判》(1999)、《道法自然——存在论的构成原理》(2001)、《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2009)、《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2014)、 《超越审美现代性——从文艺美学到政治美学》(2017)、《岚室寻踪——张盾哲学自选集》(2018)。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社会科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他的研究成果2011年获首届萧前哲学基金优秀论文奖;2013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年获第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获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张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2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超越审美现代性——马克思政治美学研究”(2013),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史渊源研究”(2015),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传承关系研究”(2007)等。
记者:老师您好,您早年毕业于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历史系历史专业,那个时候的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转向了哲学研究?您的哲学学术生涯是从自学开始的,您觉得这种学习和研究经历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张盾:我是1978年进的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历史系历史专业。当时吉大给我的印象是简朴宁静。那是一个纯真年代,当时最好的学生都聚集到文史哲这里。我们在历史系,一门心思就是学习怎样做学问。我们的那些老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李时岳老师,他是南方人,搞中国近代史已是大家,当时我们都崇拜他。他的才华,他讲课时那种内在的激情,他发表的那些漂亮论文,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植入到我的生活和生命里,变成我一生的目标和动力,从来没有改变过,虽然他不是我的“亲老师”。后来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再拿学问当真了,但我始终没有改变。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历史系77级的同学都专心搞历史专业,78级的同学喜欢哲学,看哲学书。因为当时我们班有几个很棒的同学,有哲学素养,说出的话和写出的论文和我们都不一样,那个对我转向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说到自学哲学,我的哲学确实是自学的。说到这种学习经历有什么特别意义?我觉得是这样:高等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只要你真喜欢,有那个性情,也有那个才智,就可以学哲学,不在于你是不是哲学系出身。我们有些最好的学生就不是哲学系出身,当然孙老师、赵汀阳都是哲学系出来的。关键在于,我觉得哲学这个行当比较特殊,真正哲学学得好、做得好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是天命所归,命中注定。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学历史是进入人文科学的一个非常好的入口,因为历史学是一个非常基础性和综合性的学科,学历史的人改学文科哪个学科都问题不大,我就借了这个力。再遇上一位有才华、有性情的老师,和一些有天赋、有根器的同学引导着你,然后你自己也是有性情、有实力的人,又真喜欢,这样就可以做哲学了。所以我很是感恩,在大学时期遇到了好老师,又遇到好同学,就这样注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记者:纵观您的哲学研究,您早期主要就是进行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研究,您怎样看待这段学术经历对您整个学术研究的影响?
张盾:这个学术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我80年代喜欢分析哲学,90年代又喜欢上现象学(主要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和中国学术界的趋向大致一致:80年代分析哲学热,90年代现象学热。不过我是自己在家里看书,工作就是在《社会科学战线》当编辑,很自由,有大块时间读书。我迷上分析哲学,是因为我们班有个同学田立年,他在我们班年龄最小,当时被我们认为是哲学天才,后来考到复旦学现代西方哲学读硕士,回来他跟我说:“分析哲学是最正宗的学院哲学。”我看的第一本分析哲学的书是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清晰、简洁、漂亮但决不肤浅,把深刻的思想创见和明晰的表达方式结合在一起,特别适合初学哲学的年轻人。我当时很快沉醉其中,找来了几乎所有汉译的分析哲学著作看。后来我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无须存在公理的指称理论》,发表在1989年《哲学研究》6期,那个不是研究分析哲学,而是模仿分析哲学的方式和笔法去讨论一个实在论和唯心论的关系问题。我跟分析哲学的缘分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分析哲学在我心里的剩余物就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很早就有汉译本,田立年又送了我一本英德文对照本的《哲学研究》,这是我看得最完整最认真的一本外文原著。分析哲学教会了我怎样写论文,怎样写漂亮的论文,我写了一批哲学论文,最后成为《分析的限度》这本书。

后来我读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发现比所有分析哲学都写得好,我又开始迷恋康德。但《纯粹理性批判》就是看不懂。1993年,我买到韦卓民《纯粹理性批判》译本,品相不好,但我如获至宝,我读了又读。读懂《纯粹理性批判》的感觉对我来说终身难忘,那是我30多岁时的一个金色黄昏,那天儿子在外面玩耍,妻子在厨房操劳,我在卧室突然看懂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看懂这本书的第一感觉就是它写得太美了。然后就是现象学,就是胡塞尔的《大观念》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还有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很多年里我反复读这几本书,关注里面的每一个细节,但几乎没写过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我这种做法,按西哲界的标准可能根本算不上“搞”德国古典哲学或者现象学研究,但我感觉自己确实从这几本大书里学到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简单讲,我学到了哲学的功夫并受用终身。这就是喜欢和热爱吧。最近看了一个牟宗三品评中国几代学人的帖子,颇有感触。晚清和民国时代只有最聪明的人才去做学问,而学问这个东西恰恰需要最聪明的人倾其一生全力去做,还不一定能弄好。好学问的标志就是好作品,别的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记者:在您的学习经历中,哪个哲学家和学者对您影响最大?您觉得一个研究哲学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教养?
张盾:是这样,因为我是自学哲学,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刚才说的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根斯坦,特别是那四、五本书。晚年我比较喜欢的哲学家是阿兰·布鲁姆。国内哲学界对我有影响就是孙正聿和赵汀阳。年轻时我从赵汀阳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拥有自己的问题,并且既有想象力、又有把握地处理这些问题,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自学的过程。中年以后我又从孙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真功夫,除了怎样研究马克思,特别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学会了怎样做事和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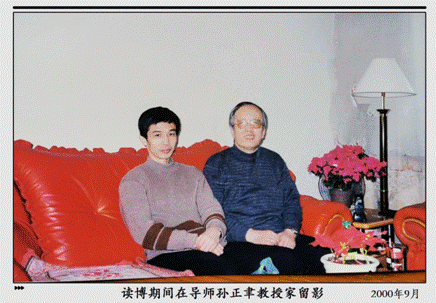
关于你说的教养,这个东西很重要,但又是无形的。以我喜欢的作家汪曾祺为例,有人说他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就是说他有那种特殊的教养,其他作家没有,我们这一代学者也没有他那样的教养:诗文书画全通,五经六艺全懂,风流倜傥,有雅好,有性情。我肯定不行。可是话说回来,即使有那样的教养也不一定能做得了哲学。哲学是很特殊的一种学问。最近有人质疑钱钟书、陈寅恪那样的学问,有一定道理。哲学是人类精神的最高技艺和境界,即使真有教养的老派文人也没有权利去蔑视像康德那样的人。就我而言,我从小就读父亲收藏的相当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书,最喜欢陶渊明、杜甫、李后主还有《红楼梦》。上大学后我又看外国文学,最喜欢托尔斯泰和帕斯杰尔纳克、福克纳和詹姆斯·乔伊斯,还有川端康成。晚年喜欢看日本电影和日剧。这算是最基本的教养吧。
记者:您曾经写过一本存在论方面的专著《道法自然》,您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能否说一下您想通过这么一本书解决什么核心问题?这本书对您的学术人生有什么意义?
张盾:《道法自然》是我生命追求中最重要的一个作品,也是我写得最艰苦的一本书。全书完全按照康德、胡塞尔式的体系建构和概念推演的方式写成,耗去了整整6年时间。《道法自然》的问题是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观性原则,要求在一个不预设任何主体性前提的新论域中重新解说存在的本意,这个新论域我称之为“存在的第三人称论域”。其实我的第一原理非常简单,我认为存在的真正本意是:凡存在总是存在者自己去存在,每一个存在者的存在都有自己的内容,这个内容必须由存在者自己去构成,与存在之外的主体无关;存在之外的主体所看到、所领悟、所创造的存在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对存在的“第一人称性解释”,其有效性取决于主体的视界和尺度,而不取决于存在者自己;然而真正说来,一个存在事态的内容是不能由思想的尺度和形式来替代的,只能由存在者自己去构成。尽管这个基本原理相当简单,但要在哲学上证明它却很麻烦,因为要在一个如此单纯的第一原理之上重建存在论的问题基础,必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我需要重新开拓出一个完整的第三人称论域去取代人们熟悉的第一人称论域,这个新论域包括重新构造主要概念,重新建立基本准则,然后用这些概念和准则处理一系列具体问题,最后还要对整个西方主体性思路进行批判。

我觉得,通过写这本书,我对曾经给我以重要影响的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乃至赵汀阳作了一个交代,即用我从他们那儿学来的功夫批判他们的主观性观点。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少数年轻人之间传播,至今我不能肯定它在多大程度上被圈内人接受,但我的哲学功夫就此练成了。《道法自然》不仅铸定了我的思维方式,而且铸定了我的语言方式,我至今仍然是按那种比较固定的方式写作和说话。之后我研究马克思,上手就很快了。可见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你真用心去做,并且做出来了,功夫没有白瞎的。
记者:近年来您的研究兴趣先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近来又转向了政治美学,在这种转向中您关注了哪些哲学问题,您对马克思哲学本身又形成了何种新的理解?
张盾:进入马哲圈,孙正聿老师是我的引路人。主要的成果就是两本书:《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和《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还有几十篇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据我所知,我的这两本书被大家接受得比较好,我那些论文也在圈内被广泛阅读。总体而言,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是这样,我认为作为一种时代精神,马克思的学说确实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有用的哲学之一,因为它是对近代以来直到今天的整个现代性资本主义体制的否定性和批判性理解,它让我们能够想象世界之为世界还可以有另一种存在方式,人之为人还能有另一种活法。为什么马克思的观点不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和经验事实所支持?我认为这是因为马克思是人类精神中的高度理想主义的产物,正因如此,只要人类的精神追求依然存在,马克思的哲学就不会失去意义。这是使马克思不朽的地方。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我个人的体会是,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最大的理论张力和学术内涵,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你的才华和功夫,想做好“马哲”不容易。反过来说,做“西哲”也是一样,如果你做不好,同样味同嚼蜡。我最近因为做美学读了柏拉图全集,我有一个体会:所谓经典学术名著就是一个场子,进去的人接过大师们的“话头”继续说话,或者叫“文本解读”,或者叫“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这里有无限的余地供你发挥自己的才华、想象力和精神力量。有的经典名著写得特别精致,比如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有的经典名著像柏拉图和马克思写得不那么精致,但却有无限丰富的意蕴,它所暗示的问题和内容几乎是无穷的,它就是个场子,你进去说话,可以无限制地发挥才华和想象力。能够进入马哲圈,我很幸运,为这件事我永远感谢孙老师,同时也感谢马哲圈的朋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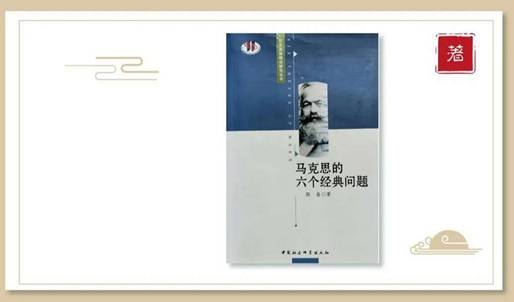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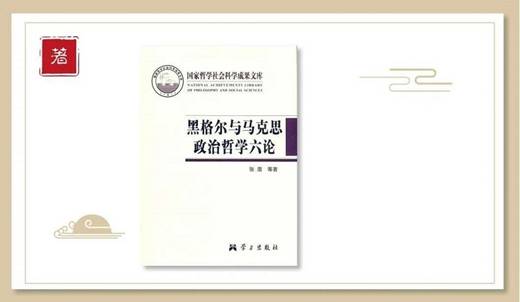
2017年,我的美学书《超越审美现代性——从文艺美学到政治美学》出版。这本书是我继《道法自然》之后又一次拼尽全力去完成的“生命作品”,以后我可能就不再写这种书了。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批判近代以来的文艺美学,大意讲在本质意义上艺术已死,文艺美学是艺术的悼词,文艺美学的艺术崇高论和审美经验论这两个教条把艺术引入歧途。第二部分追溯了艺术的原初本质是“可见之美对不可见之美的象征”, 并力主中世纪艺术是这一原初本质的最好范本。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在这一部分花费极大心血去“建构’了中世纪艺术的象征性、匿名性和实用性等美学特征,我还为此专题批判了康德的天才论美学。第三部分是回到政治美学,讲美学的原初形式就是政治美学,柏拉图最初创立的美学就是政治美学,只是他没有用“政治美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我编的。那么什么是政治美学?就是美不以艺术之美为范本,而是扩充到艺术以外的政制之美、人性之美和哲学之美。马克思把“自由联合体中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当作对制度与人性的更高真理的彻底理解,以此恢复了柏拉图对最好政治和最美人性的思考,从这一点上来说马克思学说是一种政治美学,或者说是现代柏拉图主义。

这本美学,我自认为是我这一生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也许因为它是我在思想和功力都达到成熟的晚年写出来的书,既有那种意气纵横笔力凌云的感觉,又有点“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意味。这本书从整个思想倾向来说是先验主义的,主张最好的政制与人性是一种观念创造物;从内容的风格上则是古典主义的,努力追求理性的态度、简洁的结构和庄严的气象。但这本书把马克思学说解读成一种关于最美政制和最美人性何以可能的先验政治美学,跟学界主流观点相距太远,可能让许多人不太习惯。但也有人真心喜欢它,特别是赵汀阳极其难得地说了赞美的话,说它”切中时弊“,我觉得这真是看懂了、也说中了的评语。这种政治美学确实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我坚信这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伸张马克思学说的哲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最合理方式,也许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记者:您怎样看待您整个学术研究工作的内在一致性,您是否愿意对您整个学术生涯的学术取向做一下总结?什么是您特别难忘的和值得回忆的?
张盾:要说我整个学术生涯最大的内在一致性,应该就是一生不变的对哲学和学问本身的热爱,对完美作品(不仅是自己的,也包括别人的好东西)的终生不变的迷醉。这也没什么特别崇高的意思,就是喜欢,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喜欢学问和好作品。去年我出版了自选集《岚室寻踪》,其中编选了我一生写过的自认为最好的24篇论文,我在序言中说:“这24篇论文见证了我一生追寻哲学事业的踪迹:年轻时研读分析哲学而初识功夫,中年之际苦修存在论而自谓得道,此后以所习功夫研究马克思而证其效用,晚年又在美学研究中将所得之道再次印证之——由这些篇章构成的我的学术生涯是坚实的和充盈的,然而在茫茫人世间,它又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这算是我对自己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总结吧。

学术生涯特别难忘的人和事,这辈子我出了6本书,发表了100篇论文,最难忘的就是《道法自然》和《超越审美现代性——从文艺美学到政治美学》,这两个写出来以后觉得自己做出了自己可能做出的最好学问,没有虚度此生,就是这样。还有特别难忘的就是一些老师和朋友:李时岳老师、孙正聿老师、孙利天老师,还有赵汀阳。还有就是高清海老师,我和高老师共处不多,但他的睿智、威严和谦逊让我永远怀念。还有特别难忘的就是我有幸遇到的那些有才华的学生,不能一一提到他们的名字了。
